菲律宾外劳:国家命运的另一半在异乡

2009年2月17日,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菲律宾海外就业署一个办事处内,人们排队等待办理海外就业手续
文/《环球》杂志记者 聂晓阳(发自马尼拉)
编辑/吴美娜
在耶路撒冷,我见过推着轮椅、细心照顾老人的菲律宾女佣,她们用温和的口音与病人对话,给古老而紧张的圣城增添了一丝温情;在日内瓦,我遇到过一位陪伴外交官家庭全球奔走的菲佣,她照顾着别人的孩子,一年都见不到亲生孩子几次,那种复杂的神情,既有骄傲,也有压抑的失落……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你几乎都有可能遇见菲律宾人。
典型的还包括中国香港。最近我在香港读到一个颇为荒诞又意味深长的新闻:几个菲佣在业余时间通过网络视频自学牙科知识,竟然开了一个“黑牙医”诊所。新闻令人莞尔,却也让人心头一沉。那背后是一种被迫的创造力与无奈的生存姿态——在异乡,她们不仅要照顾他人的家,还要寻找属于自己生活的出口。
“隐形”的存在
在马尼拉,有一次朋友忽然对我说,如果我有认识的合适的菲佣,可以推荐给他,因为他家的女佣已经提出辞职,准备去沙特打工。到临别时,那位才20出头的年轻女孩显得格外兴奋,眼神里满是憧憬与好奇,仿佛要去闯荡一个更辽阔的天地。
在菲律宾,这样的故事几乎天天发生。出国工作不仅是一种谋生方式,更被许多人视为一种“机会”。在马尼拉,不仅有大量专门介绍去海外务工的中介公司,大街小巷的墙壁、电线杆上也贴满了形形色色的广告:去中东做护士,去欧美当护工,去新加坡或中国香港做家政,甚至到邮轮和远洋货轮上工作。“高薪”“包食宿”“改变人生”等广告词,带着一种不容拒绝的诱惑。
接触这些菲律宾女佣与外劳,你会发现,她们普遍勤劳能吃苦,能在闷热的厨房里长时间劳作,也能在主人尚未开口之前,察觉并补上家中遗漏的琐事。而且,她们特别有分寸感,既能默默承担起繁重的家务,又懂得在交流中保持适度的克制与恭敬,不逾越主客之间的界限。许多人甚至擅长“隐形”,能在完成所有清洁、洗涤与烹饪后悄然退下,让主人几乎感受不到她们的存在。
在马尼拉的许多公寓楼里,总能见到那种小小的保姆间,面积狭窄,仅能容纳一张单人床和一只柜子。人们习惯客气地把菲佣称作“帮工”,她们在干完一天活后,往往就躲进自己的保姆间。即便里面没有空调,只有一盏昏黄的灯泡,她们也能在里面一待就是几个小时,甚至一整夜。那是一种让自己消失的姿态。她们把笑容与礼貌留在客厅,把疲惫与寂寞带回那扇轻轻关上的小门背后。

菲佣们在中国香港的郊野公园自娱自乐,跳起欢快的舞蹈
这些小小的保姆间,像是马尼拉公寓楼里的一种隐秘建筑学符号。对外籍雇主而言,那是“帮工”的专属空间;但对菲佣自己而言,却是一方属于她们的“隐身之所”。外界的嘈杂、家庭的差事、主人的目光,都在那扇门关上的瞬间被隔绝开来。她们在这个社会的空间分布中,被划分进狭小的角落,却以坚韧、耐心与习惯性的克制,将这种空间转化为自我庇护的“安全区”。
这种姿态,也延续到她们走出国门后的日常。菲律宾外劳遍布中东、中国香港、新加坡乃至欧美,你或许在商场里看不见她们,却会在清晨的地铁里看到三三两两穿着整齐、手里拎着便当的菲律宾女人。她们喜欢结伴而行,彼此交换雇主的脾气、分享转账的渠道、互相传递打听来的工作机会。这些看似零散的交流,慢慢织成一张跨越国界的劳工网络。
在这张网络中,最显著的特点仍然是“分寸感”。许多菲佣会自觉不去打听主人的隐私,不在主人朋友到访时露面。这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隐身术”。她们知道自己的价值在于“让生活更顺畅”,而不是“成为生活的中心”。
然而,这份隐身的代价是沉默与压抑。她们习惯于把情绪隐藏在狭小的保姆间,把疲惫倾诉在海外的视频电话里。每到发薪日,她们会把大部分钱寄回家乡,那些汇款支撑着孩子的学费、父母的药费、兄弟姐妹的小生意。可以说,菲律宾的外劳群体,用自己的辛苦工作,维系着一个家庭,甚至是国家的经济命脉。
漂泊在外
“我们是一个到处都在漂泊的民族,”一位马尼拉的学者曾这样对我说。我更愿意把这看作是一种“离散文化”,一种遍布全球的迁徙与牵挂之中生成的菲律宾特色的乡愁。这种“离散文化”并不是偶然形成的,而是带着明确历史印记。
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冲击全球,菲律宾国内经济停滞。1974年,马科斯政府颁布《劳动法典》,第一次把“海外就业”写入国家政策。那一纸法律,从此成为一条深刻改变无数家庭命运的分水岭。从那时起,走出国门成为国家鼓励、制度推动的出路。80年代,政府又设立了海外就业署,集中管理劳工派遣,把原本零散的务工潮流,变成一条有章可循、规模庞大的迁徙之路。

2003年3月26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一名菲律宾籍工人在一座在建楼房里砌墙
根据各类统计,目前约有1000万菲律宾人长期在海外生活,相当于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他们中有人早已成为移民,定居在北美、欧洲或澳大利亚;也有人以合同工的身份漂泊在外,被统称为“海外菲律宾劳工”。菲律宾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2023年,有超过200万人持短期或长期工作合同,在全球各地谋生。
也就是说,“1000万”是常年散落在世界各地的菲律宾人群体,那“每年200万”,则是这支离散大军不断更新的流动部分。数字背后的差异,其实揭示了菲律宾离散文化的独特形态:它不是单向度的出走,而是一种持续的流动。许多菲律宾外劳签的合同只有一年或两年,到期之后,他们可能回到故乡休整一阵子,又再次启程去往新目的地。一份简历,几乎就是一张小小的世界地图。
这种流动性让“归乡”成为一种不稳定的概念。每一次回国,都只是“中场休息”。等到下一个合同到手,分别立刻到来。父母在外漂泊,孩子在家乡长大;兄弟姐妹多年聚少离多;夫妻常常在机场分别又相聚。这种节奏,慢慢塑造了一种特别的家庭观念:感情不是每天的陪伴,而是靠寄回来的汇款、视频通话里的问候以及节日时的一顿团圆饭来维系。
也正因为如此,菲律宾的“离散文化”带着一种迁徙的底色。它不同于那些一去不回的移民故事,而更像一种循环往复的航行。就像古代海上的商旅,他们离开港口,远行数年,带着货物与消息归来,然后又再次出发。只不过,如今“货物”换成了汇款,归来的“消息”是世界另一端的生活片段。
“想象的共同体”
这种迁徙感,甚至延伸到整个社会心理。菲律宾是一个宗教气氛浓厚的国家,但在祷告之外,人们更熟悉的是离别和等待。这个国家的现代经验,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这种不断地出走与回归之中被塑造的。在几乎每一个菲律宾家庭都有亲人在外漂泊的环境下,菲律宾不只是一个地理上的群岛国家,更是一种遍布全球的“想象的共同体”。这些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劳工、护士、海员和家政人员,用他们的身影,把“群岛”延伸成了全球网络。
无论身处何地,只要有菲律宾人在,就能生长出一个小小的社区。在洛杉矶的天主教堂,每到周日弥撒,外劳们会穿着整洁的衣服聚在一起,唱起熟悉的圣歌,那旋律瞬间把人带回马尼拉的街头。新加坡的植物园里,休假的女佣们席地而坐,打开从家乡带来的塑料饭盒,里面是腌鱼、烤猪肉、拌上酱油和醋的米饭。她们一边吃,一边聊孩子、父母、老家村里的新鲜事。
这样的场景几乎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能见到:在多伦多的冬夜,几个外劳聚在出租屋里煮热汤,唱卡拉OK;在中东的工地宿舍,工人们把旧吉他传来传去,唱起流行的塔加洛语歌曲;在罗马的广场上,菲律宾护士们下班后相约合影,身后是古老的石柱与喷泉。只要听见熟悉的歌声或语言,菲律宾人便会立刻聚在一起,分享食物,分享故事,分享思念。
这种“分享”不仅是情感的慰藉,也是一种文化的延续。身在他乡的菲律宾人,常常通过节日把社区凝聚起来。圣诞节是最隆重的时刻,即便是在沙漠中的宿舍,他们也会找来彩灯、纸星和简陋的圣诞树,把冷清的空间点亮。有人说,菲律宾人的离散文化,就像椰子树的种子,无论漂落到哪个海岸,都能扎根、生长、开花结果。
菲律宾中央银行的数据显示,海外劳工寄回的汇款常年维持在数百亿美元的规模——2024年甚至突破383亿美元,占到国民经济总量的八分之一左右。经济学家称它是“无形的支柱”,是国家外汇最稳定的来源。因此,对于很多菲律宾人来说,全球化不是抽象的经济概念,而是切身的生活经验:母亲在香港,父亲在利雅得,孩子在马尼拉,亲情拉扯跨越半个地球。
离散不仅是经济现象,更是一种文化。在菲律宾的歌曲里,离别和思念是反复吟唱的主题。20世纪70年代,歌手Freddie Aguilar的一首《Anak》(《孩子》),唱出了父母对子女的叮咛与惆怅;到21世纪,许多流行歌曲和卡拉OK必唱曲目,仍然围绕着“远方”“回家”“思念”。
电影里,2008年的《Caregiver》(《看护》)曾在菲律宾引起轰动。片中,莎朗·库内塔饰演一位中学教师,为了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不得不放弃自己熟悉的讲台,前往伦敦做护理员。她在异国医院里摸索、忍耐、被轻视,也一次次在夜深人静时掩面而泣。可当她把工资寄回家乡时,又会在电话里装作轻松,只说“我很好”。这种挣扎与孤独,让影院里无数菲律宾观众默默拭泪。
文学作品中,这样的叙事更为丰富。菲律宾著名诗人何塞·加西亚·维拉早年就描写过流亡与漂泊。当代,像杰西卡·哈格德恩的小说《食欲》,则把菲律宾人的离散命运与国家历史、政治记忆交织在一起。许多年轻诗人也把海外劳工的思念写进短诗:机场、汇款单、电话、时差,成为他们诗句里的常见意象。
在这些作品中,“离开”不是选择,而是一种命运;“归来”并非圆满,而往往伴随着陌生与裂痕。文学和电影之所以能打动菲律宾人,是因为它们再现了整个社会的集体经验: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一个人在海外,都有关于离别和重逢的故事。
“我的家人需要我”
离散还改变了菲律宾的身份认同。菲律宾人常说:“我们有两个家,一个在这里,一个在那边。”这种跨洋的生活,让他们更容易理解多元,也更容易感受孤独。我曾在米兰的一家小餐馆见到过一位菲律宾厨师。他说自己已经在意大利待了20年,孩子也在这里上学,可是他仍然坚持寄钱给回马尼拉的父母,供他们在每年台风后修房子使用。“我不知道我到底算哪里的居民,”他说,“但我知道我的家人需要我。”

2003年3月22日,在设在菲律宾总统府内菲外籍劳工家属免费电话中心,一名老妇人和她的孙子、儿媳妇在给国外工作的亲人拨打电话
离散还对菲律宾社会产生了更深的影响。它塑造了一种“跨洋的家庭结构”。许多家庭成员长期不在国内,家里的抚养责任落在祖父母或亲戚身上。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常常缺少父母的陪伴,这些“留守儿童”更容易出现孤独感、被遗弃感以及身份认同的困扰。他们在电话或视频里叫着“爸爸”“妈妈”,却在现实生活里对父母的形象渐渐模糊。久而久之,亲子关系变得疏远,而这种裂痕往往要等到孩子成年后才被真正看见。
同时,它也强化了“汇款依赖”的经济模式。海外汇款的确改善了无数家庭的生活条件,从住房、教育到医疗,都因此得到保障。但也让菲律宾经济过度依赖外部收入,一定程度上拖慢了国内产业的升级与创造力的培育。这个矛盾在中吕宋的一个小城市里有过生动的注脚:那里有一座像体育馆一样大的咖啡馆,每到周末几乎座无虚席。朋友告诉我,这座城市几乎家家有人在海外打工,正是海外汇款支撑起了这里的消费热潮。如果没有外劳,整个城市的餐饮业恐怕会瞬间萎缩。
当然,离散也让菲律宾在某些方面更加强大。每一次出国,都是一次文化的交流与回流。海外劳工不仅带回金钱,还有观念与习惯。加拿大的护士带回社区医疗的理念;中东的家政工人学会尊重不同宗教节日;意大利的工人掌握新的手艺。这些经验在菲律宾社会中长期积淀,形成一种跨洋性格:既扎根于本土,又与全球紧密相连。
离散也让这个国家在一次次的离别与重逢中,学会了坚韧,并拥有了更广阔的世界感。它把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片段重新联结,也让这个群岛国家在漂泊中保持完整。它是菲律宾的痛,也是菲律宾的力量。
马尼拉机场大厅里总是挤满了人。有人笑,有人挥手告别,有人则默默垂泪。这样的场景,仿佛在诉说一种集体的命运。漂泊让菲律宾的根须伸向世界。这个国家也许永远都会有一部分人在远方,他们用金钱、用记忆、用文化,把故乡与世界编织在了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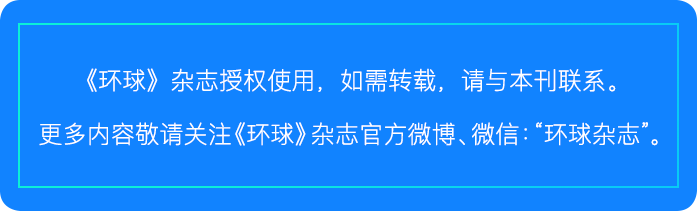

 手机版
手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