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IT产业面临重大转折

2月10日,在法国巴黎总统府爱丽舍宫,法国总统马克龙(右)与印度总理莫迪准备出席欢迎晚宴。为期两天的人工智能行动峰会10日在法国首都巴黎的大皇宫拉开帷幕
文/毛克疾
编辑/胡艳芬
最近发布的一个消息,正强烈刺激着印度IT产业的神经。印度最大IT服务企业塔塔咨询公司(TCS)宣布史上最大规模裁员计划——到2026年3月将裁撤1.2万个岗位,约占员工总数的2%。这一决定不仅令数以万计的家庭陷入不安,也让整个印度社会第一次直观而强烈地感受到“人工智能(AI)冲击”可能带来的影响。
此外,今年初开源大模型“深度求索”(DeepSeek)横空出世,以开源模式,以及低成本、高效能的特征震动全球,让印度业界不禁自问:为什么这样的突破诞生在中国,而不是素以IT产业闻名的印度?
长期以来,以IT为主的服务业出口是印度经济的支柱产业,不仅带来大量外汇、就业机会,还成为印度的骄傲。然而,在AI浪潮下,这一支柱产业正在经受严峻考验。面对技术替代、地缘政治摩擦以及全球产业链深度重塑,印度必须回答一个关乎未来的重大问题:这艘以“人力优势”著称的IT巨轮,将在AI时代保持航向,还是迷失于风暴中?
印度“服务神话”的光环与阴影
要理解当下印度IT产业的深度焦虑,就必须回溯其过去30多年的发展轨迹。
20世纪80年代,印度逐渐走上一条不同于东亚地区“先制造、后服务”的发展道路。通过政策扶持并深度利用劳动力禀赋,印度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产业跳跃”——绕过大规模工业化,直接走向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在印度1990年代实现经济自由化之后,IT服务业几乎一夜之间成为印度最具国际竞争力的名片。
真正让印度声名鹊起的是世纪之交的“千年虫危机”。当时,全球软件系统普遍使用两位数字表示年份,因此2000年的到来可能导致程序错乱,导致大规模系统瘫痪。面对这一紧迫的威胁,大量跨国企业不得不寻找外包伙伴。这时,印度程序员凭借廉价的IT服务、流利的英语表达能力,以及高度服从的工作文化,一举承接全球海量的程序修复订单,成为公认的“可靠后台办公室”。这不仅为印度带来可观的外汇收入,更是为印度赢得了在全球IT服务市场的声誉。
印度政府敏锐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相继采取设立软件产业园、出台出口补贴政策、豁免硬件关税、推动技术引进的政策措施,为印度IT产业快速壮大提供了保障。塔塔咨询(TCS)、印孚瑟斯(Infosys)、威普罗(Wipro)、马恒达科技(Tech Mahindra)等企业在这一时期迅速崛起,业务遍布欧美,奠定了印度“服务外包大国”的基础。
印度IT服务业自此保持了长达30年的高速增长。1993年至2022年间,印度服务业出口以年均14%的复合增速扩张,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到2022年,印度已成为全球第二大IT服务出口国,仅次于爱尔兰,占全球15%的市场份额。更重要的是,这一产业极大缓解了印度长期的贸易逆差,为国家经济稳定提供了关键支撑。正因如此,印度成为后发展国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发展样本。
印度模式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巧妙避开了制造业对基础设施的高要求。相比需要铁路、公路、能源网络全面支撑的工业化,IT服务业只需点状的现代化园区和宽带网络即可运营。更关键的是它绕开了印度僵化的劳动法,最大化发挥了“英语+低成本+规模化”的人才优势。这一独特生态位,既让印度在全球产业链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也为无数青年带来了阶层跃升的机会和体面的工作。
然而,光环背后也有隐忧。印度IT业的崛起更多依赖“人力套利”,而非自主创新——它源源不断向全球市场输送低成本的程序员劳动力,却鲜有具有原创性的技术与产品。这种模式在过去30年有效,但当AI浪潮袭来,似乎正变成一种新的“资源诅咒”。
创新短板与“人力困境”
尽管印度IT产业在全球市场十分耀眼,但一个尴尬的事实始终无法回避:印度是世界的“后台”,却从未成为创新的“前台”。

图为印度举行软件展
30年来,印度业界几乎没有推出一款在全球市场叫得响的原创软件——没有自主品牌的操作系统、浏览器、社交媒体平台,也没有形成类似思爱普(SAP)、甲骨文(Oracle)那样的企业管理软件体系。除了Zoho(印度知名办公软件公司)和Finacle(印度软件巨头印孚瑟斯开发的银行核心系统解决方案)在细分领域拥有一定影响力,大多数印度IT企业都停留在“服务供应商”的角色。印度在外包链条中守着相对稳定,但缺乏深度的利润。
学界甚至用“错过所有快车”来形容印度IT业的发展轨迹。从桌面软件到移动应用,从社交网络到短视频,每一波数字经济浪潮都未能在印度孕育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型IT企业。就算是在印度国内市场,局面也从未改变。当TikTok被莫迪政府以安全理由封禁后,印度本土曾出现大量模仿应用,但大多为粗制滥造,用户体验感差,最终只是昙花一现。这种原创产品的系统性缺位,反映出印度体制与模式的深层问题。
客观而言,印度IT人才在国际市场上的确供不应求。印度最优秀的相关专业毕业生往往第一时间被硅谷、华尔街的高薪岗位招走,从微软、谷歌到到奥多比(Adobe),印度裔高管比比皆是。剩下的中高端人才则被跨国公司在印度诺伊达、古尔冈、班加罗尔的研发中心直接雇用。印度本土企业虽然吸纳了庞大的程序员群体,但多集中在低附加值岗位。人才的“虹吸效应”导致真正具备创新潜力的精英难以扎根本土,形成严重的“脑力外流”现象。
更深层的矛盾在于,印度企业缺乏对创新的激励。塔塔咨询、印孚瑟斯等巨头在垄断性市场结构下已经形成稳固的盈利模式。它们更愿意通过扩充人力规模来满足客户需求,而不是冒险进行投资研发;宁愿雇用低技能劳动力拉长项目周期,也不愿投入高技能人才以提升效率。这导致大量程序员陷入重复性工作,而整个行业被锁死在低端服务的链条上。
数据最能说明问题。2024年,印度研发支出仅占GDP的0.65%,产值约254亿美元。对比我国科技部的统计数据,2024年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3.6万亿元人民币(约合5053.5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2.68%;在美国,基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研究报告,2023年全美研发投入为9400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3%到3.5%,据此推算,2024年全美研发投入约为9700亿美元,占GDP的比重约3.3%。
而且,印度的差距不仅体现在绝对规模上,还体现为研发文化与生态的缺失。印度缺乏完整的创投-研发-产品化链条,也没有足够的风险资本支持初创企业,因此即便有创新和研发的想法,也常常因融资困难和市场垄断被扼杀。
在这样的环境下,印度IT企业很少冒险进入新兴领域。它们更像是“工时工厂”,按需为西方客户提供劳动力,而不是“创新引擎”。
这一困境的代价正在显现。对印度年轻人来说,进入IT行业曾是跻身中产阶层的绿色通道,但随着工资增长停滞与AI替代加速,这一梦想正在破碎。与此同时,制造业发展不足,使得印度缺乏为这些青年提供替代就业的产业支撑。
可以说,印度IT产业的辉煌背后,其实是一种以“低成本劳动力”为核心的商业模式,而非以“技术创新”为驱动的产业逻辑。这种模式一旦遭遇AI的降维打击,其脆弱性将全面暴露。
AI与地缘政治的双重冲击
如果说过去30多年印度IT产业的成功依赖于人力成本优势与全球化红利,那么在2025年之后,这两个支撑点已同时动摇。人工智能技术迅速进化,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保护主义政策大行其道,正在酝酿一场可能改变印度未来的严酷风暴。
长期以来,印度程序员被视为“低价高效”的劳动力资源。无论是代码调试、数据库管理还是技术支持,印度企业都能用远低于欧美的成本完成任务。然而,这一优势正在被AI迅速侵蚀。ChatGPT、Claude、Gemini等生成式AI工具,已经可以高效完成过去由大量印度程序员承担的重复性工作。这些工具能够以更快、更便宜的方式完成大量外包任务,让印度的“人力差价”优势瞬间蒸发。
TCS宣布裁员1.2万人的消息,就是AI替代效应的一个缩影。虽然TCS没有明确提及AI,但业界普遍认为,这正是自动化和智能化驱动的结果。今后,企业仍需要人类程序员,但主要集中在复杂、创新和战略性岗位,而对中低端、重复性的岗位需求将大幅下降。这意味着,印度庞大的IT就业人口可能面临“结构性失业”。
事实上,AI对印度IT产业和从业者造成的冲击并非突如其来。2015年前后全球AI热潮就已显现,但印度IT巨头并未积极应对。它们沉浸在庞大的人力外包市场中,靠低成本劳动力套利获得稳定利润。
除了技术冲击,印度还不得不面对来自最大市场——美国的政策打击。印度IT服务业出口的一半以上依赖美国客户,塔塔咨询、印孚瑟斯等巨头超过60%的收入来自北美市场。这种过度集中于单一市场,一直是印度模式面临的风险。
2025年7月,特朗普政府对印度商品加征25%的关税,8月底更以涉俄贸易为由进一步将对印关税提高至50%。虽然这些措施主要针对货物贸易,但随之而来的政治氛围又深度波及印度服务业。不久后,美国参议院推出《阻止就业岗位国际转移法案》,拟对所有外包服务加征25%的税费,其直接目标就是阻止企业将岗位继续外包给印度等低成本服务提供国,以此推动“就业回流”。
如果这一政策落地,印度IT企业将首当其冲受到影响。不同于制造业可以通过多国布局转移产能,服务业外包的链条更短、更集中。一旦美国市场出现壁垒,印度难以快速找到替代市场。换句话说,印度很可能失去赖以支撑出口的半壁江山。
事实是,AI的兴起正在帮助美国完成“服务业回流”。过去,美国企业将大量后台工作外包给印度,是因为后者成本优势显著。但如今,AI能够在本土完成许多任务,再辅以保护主义政策,外包的必要性正在迅速下降。虽然特朗普最看重的是“制造业回归”,但AI正让“服务业回归”更具现实性。比起高投入的制造业,服务业回流的门槛更低、速度更快,对就业的带动也更直接。对印度而言,这无疑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冲击。
AI和美国政策的双重冲击,使印度IT业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对印度来说,这不仅是产业挑战,更可能演化为社会与政治危机。目前,印度IT产业直接就业人口超过540万,间接带动就业达数千万。如果大规模裁员潮蔓延,青年失业率势必攀升。考虑到印度已面临超过8%的失业率,这一数据攀升可能引发更广泛的社会不满,带来更大政治压力。
更严重的是,IT服务出口是印度弥补货物贸易逆差的关键支柱。2023年,印度服务出口达3250亿美元,抵消了约2500亿美元的货物贸易逆差。如果这一支柱动摇,印度可能面临外汇储备压力、卢比贬值与输入性通胀等连锁反应。这不仅关系到经济稳定,更直接影响莫迪政府的执政前景。
应对措施与未来选择
面对上述压力,2025年以来,印度政府和产业界已启动一系列“紧急应对”措施,试图挽救摇摇欲坠的IT神话。
在“深度求索”引发震动后仅10天,印度电子与信息技术部(MeitY)便宣布启动国家级AI计划,公开征集多用途大模型的研发提案。政府协调信实工业、塔塔集团等财团贡献算力,并以补贴价格从私营云服务商和数据中心调集近1.9万个GPU,用于科研团队开发本土模型。其决策之果断、速度之快,在印度科技史上并不多见。
然而,问题也显而易见。印度高等教育体系培养了大量合格的程序员,却未能形成一支能够与国际顶尖研究团队竞争的科研群体。尽管政府对算力进行补贴,但缺乏原创性算法、语料库和应用生态,将印度的AI发展焊死在“追随者”层面。
在企业层面,一些印度IT巨头也意识到转型迫在眉睫。印孚瑟斯和维布络(Wipro)相继宣布,在未来3年内加大对AI研发与员工再培训的投入,尝试从“人力外包”向“智能外包”过渡。塔塔咨询则提出将更多资源投入到高端咨询和系统集成业务,减少对低端编程工时的依赖。
同时,跨国公司在印度设立的全球能力中心(GCC)也可能成为转型突破口。这些中心不仅负责后台支持,还逐渐承接研发、法律和财务等高附加值任务。如果印度能够借这些平台提升本土人才的能力,推动知识溢出,也许能逐步摆脱“低端锁定”的困境。
不过,转型的代价不可低估。数百万个依赖低技能岗位的从业者,如何在短时间内适应AI时代的要求?再培训和技能升级不仅需要巨额资金,更需要教育体系和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若无法实现平稳过渡,大规模的“人才错配”将成为印度社会的潜在隐患。
对印度而言,当前所面临的不仅是一次产业危机,更是一次对国家战略的考验。一位印度行业专家说:“深度求索也许是对印度最好的提醒。它让我们明白,不能再把过去的成功当作未来的保证。”
印度IT业的未来,最终取决于它是否愿意真正拥抱和赶上以创新为核心的当今时代。
(作者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助理研究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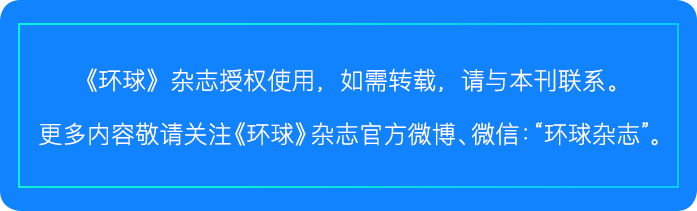

 手机版
手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