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瓷新生
文/桂涛
编辑/胡艳芬
朋友喜欢收藏瓷器。他的案头摆放着一枚圆形瓷镇纸,釉色洁白,瓷胎细腻如玉,镇纸上青花双圈纹,圈内书一“茶”字,笔意清雅。
瓷镇纸盈盈一握,小巧可爱。我本以为这是他从哪里买来的文创产品,他却笑着让我拿起来仔细看看。拿过瓷镇纸,翻转过来,赫然看见背面也是青花双圈纹,里面两行字是繁体的“金箓大醮坛用”。
我一下子明白了,这并非一枚镇纸,而是明代的一枚瓷杯杯底残片。“金箓大醮坛用”六字款表明它是当年崇尚道教的嘉靖皇帝从景德镇定制、在内殿举行斋醮仪式时在祭坛上使用的瓷杯。不知当年景德镇的窑火为这位皇帝烧制了多少青花法器,它们在香烟缭绕中承载过多少长生祈愿。朋友特意将珍贵却残破的碎瓷片打磨抛光,当作一块镇纸来用。
残损恰恰赋予了它新生。
我竟然被一只残杯底施了“障眼法”,将“局部”误认为是“整体”。但这块残瓷却将我引向一系列有趣的问题:残破的艺术品还是艺术品吗?艺术品的残片还有艺术性吗?当艺术品的残片重新成为一件“完整”的艺术品,它的艺术价值是变大了还是变小了?
如果将这些问题上升到哲学层面,也许是:“破碎”是毁灭物的手段,但是否同时也是转化与重塑的方法?如果“破碎”本身也能让艺术品重生甚至超越它脱离的本体,那是否可以说,艺术品的损毁并不意味着终结,反而有可能是它的一次升华?
卢浮宫里的“断臂维纳斯”(即“米洛斯的维纳斯”)也许是对这些问题的一种回答。残缺,赋予了曾经完美无瑕的神祇雕像更加独特的魅力。“部分”成为一个新的“整体”,产生了新的意义。
我想起在济南灵岩寺,有一件更为奇特的“残器”——铁袈裟。这尊两米多高、立于地上的袈裟形铸铁锈蚀斑驳,因其残缺更显禅意,被历代文人墨客所瞻仰。游人至此,看见这“自地涌出”、浑然天成、佛性十足的铁袈裟,不由得心生敬意。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曾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郑岩在其著作《铁袈裟:艺术史中的毁灭与重生》中有段考证:其实“铁袈裟”原本是唐朝所铸金刚力士像的下半身,铁像在唐武宗会昌灭佛后被毁,只留一片残铁。千余年来被赞颂仰望的“铁袈裟”根本不是完整的僧衣,而只是一块残片。残损,引导人们用新的方式去审视与欣赏,最终“局部”被赋予新的意义,成为“整体”。
或许这本就是艺术的一个题中之义。就像禅宗公案里的花瓶,打碎后才能看见内在的虚空,给人以启示。
瓷杯破损,失去盛水功能,它的价值却重生于残瓷片上纹饰与款识所代表的历史。这块残瓷镇纸压住朋友的文稿,也压住了他浮躁的日常。每当阳光掠过青花笔迹,“金箓大醮坛用”的庄严与“茶”字的闲适,便在纸影间交织。
真正的艺术也许从未被“完成”,也从不能被“破坏”,它只是在破碎与重组中,不断以与时代合拍、共鸣的新面目出现,产生新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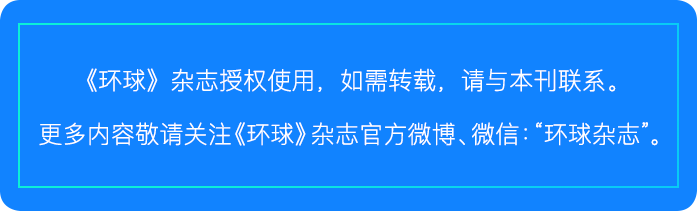

 手机版
手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