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因何一路强硬

9月29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白宫,美国总统特朗普(右)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
文/王晋
编辑/吴美娜
手拿一张中东地图,宣称多个“敌对势力”领导人已被或将被以军清除,并用马克笔对相应国家一一划勾——这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被镜头记录下的一幕。在他发言前,众多联合国会员国代表起身离席,以示对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战争暴行的愤怒。
这样的经历,对内塔尼亚胡来说不是第一次,只是这一次场面更加难看。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说,此次可能是以色列总理面对过的最为于己不利的联合国大会,以色列在全世界的地位从未像现在这样岌岌可危。
自2023年10月7日巴以冲突爆发以来,随着以色列在中东多个点位的持续出击——战线广布至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黎巴嫩、叙利亚、伊朗、也门、伊拉克甚至卡塔尔等地,这种咄咄逼人的对外行径,极大改变了中东地区的战略平衡,域内外抗议声浪持续上升。
眼下,一份加沙停火协议在多方斡旋下达成,这会是以色列行动的终点吗?
“大以色列”之梦
“有几代犹太人梦想着来到这里,也有几代犹太人将在我们之后来到这里。”在以色列政府准备将军事行动扩展到整个加沙地带之际,内塔尼亚胡8月12日接受以色列i24新闻台采访时谈到,他正在执行一项“历史性和精神性使命”。在采访中,以色列议会前议员沙龙·盖尔向内塔尼亚胡展示了一枚印有“大以色列”地图的护身符。当被问及是否与这一愿景有联系时,内塔尼亚胡回答:“联系紧密。”
在以色列历史上,对于“大以色列”的描述版本众多,从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到如今的以色列右翼阵营政治人物,对以色列的边界范围都有着不同的认知。一般而言,“大以色列”范围主要包含以色列本土,以及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加沙、埃及的西奈半岛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等1967年后以色列占领的地区。
土耳其广播电视总台网站报道指出,“大以色列”概念是内塔尼亚胡所属的执政党利库德集团政治传统的核心原则之一。内塔尼亚胡多次反对建立巴勒斯坦国,批评者认为,他的政府非法扩建定居点的行为体现了这一愿景。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加沙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是以色列加速实施这一计划的尝试。批评者形容以色列政府的做法是追求“最大土地,最少阿拉伯人”。
以色列1948年建国后,关于其国土边界该如何确定,一直是以国内的热议话题。一些以色列学者和政治阵营,如以色列工党,在领土问题上主张采取务实和理性姿态;而右翼和极右翼政治力量,如20世纪70年代崛起的利库德集团,则寻求扩张土地,尤其是将约旦河西岸、东耶路撒冷和加沙地带扩展为以色列的领土。

2月18日,以色列士兵在黎以边境黎巴嫩一侧巡逻
近些年,随着以色列政坛“70后”少壮派政治人物快速崛起,加之以色列人口结构的迅速变化,右翼和极右翼支持者在以国内占比增大,有关以色列谋求扩张土地、建立“大以色列”的呼声甚嚣尘上。这种声音认为,以色列面临的冲突范围已从传统上的“南防哈马斯,北防真主党”升级为“七线作战”,即同时在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黎巴嫩、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和伊朗应对威胁。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多数战线上都可谓斩获颇丰,大大压缩了其眼中威胁者的活动空间,重挫对方行动能力。
除了打击地区主要对手,以色列还对其他一些地区国家发出威胁,如卡塔尔。卡塔尔是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进行加沙地带停火谈判的主要斡旋方之一,以色列9月9日空袭身处卡塔尔首都多哈的哈马斯领导层,5名巴勒斯坦人和1名卡塔尔安全部队人员在袭击中丧生。此举招致国际社会强烈谴责。以色列此次打击行动,侵犯了卡塔尔的领土主权,也给本就脆弱的国际和地区形势进一步增添了风险。
内塔尼亚胡政府战略动力
内塔尼亚胡在9月26日的联大发言中为以色列在加沙地带以及中东多国的军事行动辩解,称反对巴勒斯坦建国不仅是他本人及其领导执政联盟的政策,也是以色列的“国策”。
他表示,以色列将消灭哈马斯,此举“将有助于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以色列已与叙利亚进行“认真谈判”,以色列与黎巴嫩实现和平“也是可能的”;以色列是“替美国和欧洲国家”打击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朗。
内塔尼亚胡抨击多个国家近期承认巴勒斯坦国,把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谴责归咎于所谓“反犹主义”等因素。他还对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持否定态度,声称巴勒斯坦人并不想在以色列旁边建立国家,也不相信“两国方案”,而是想要建立一个“取代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国”。他认为,多国近期承认巴勒斯坦国是“大错特错”。
这种表态虚实结合,极尽自我包装之能事。在观察人士看来,内塔尼亚胡政府这种咄咄逼人的对外战略或行动,是以色列国内政治博弈、政党利益和社会舆论的综合体现。
本届以色列政府于2022年11月赢得大选,由右翼和极右翼政党组成的执政联盟组建而成。由于其鲜明的政治底色,这一联盟常被描述为“以色列史上最右政府”。在右翼和极右翼主导的政治氛围下,对外扩张尤其是对所谓安全威胁的强硬应对,成为这届政府的首要外交目标。因此,当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特别是在爆发之初,右翼和极右翼势力要求采取政府强硬措施的呼声迅速高涨。而且,每当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展开斡旋、希望尽快结束冲突时,右翼政党往往出面阻挠,并以退出政府相要挟。
如2025年7月以来,随着国际社会斡旋力度的加大,已经有过不止一次类似举动的以色列财政部长、极右翼政党成员斯莫特里赫多次威胁要退出政府,迫使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内阁推动有关扩建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犹太定居点的计划。
对于内塔尼亚胡本人而言,冲突的延续也确有一定政治益处。由于针对内塔尼亚胡的贪腐审判仍在进行中,其领导的政府希望在司法层面推动改革,赋予政治人物更多司法豁免权,并尽力压缩以司法机构,尤其是最高法院和总检察长办公室的权限。因此,战事的延续意味着内塔尼亚胡的行政权力得以维系。
社会舆论方面,新一轮巴以冲突的爆发对以色列公众造成剧烈冲击。尤其是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遭受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以国内舆论明显“向右看”,这为内塔尼亚胡政府采取强硬对外政策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回归理性需要时间
目前总体而言以色列依旧维持着强硬基调,但结合多方面形势的变化可以判断,以色列对外政策可能正逐渐回归理性。
首先,以色列国内舆论已出现较为明显的变化。连月来,尽管多数民众仍倾向于支持在加沙地带继续推进军事行动,但对于战争手段能否最终有效实现既定战略目标的质疑声日益增多。根据以色列一家权威机构今年9月公布的数据,约有64%-70%的受访者表示支持接受一项能够确保所有人质获释并结束战争的协议。
其次,目前以色列的主要战略目标可以说都已达到,可以“见好就收”。两年战事过后,以色列周边主要“安全威胁”已逐个被拔除或削弱,以色列有余地和空间可以较为理性和客观地重新评估地区威胁与以色列国家安全的关系,其持续发动军事打击行动的动力相应有所减少。
第三,以色列国际压力增大,不得不认真思考自身面临的外部环境。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狂轰滥炸,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持续不断推进犹太定居点建设,已严重影响了巴以和平的根基。国际社会力挺巴勒斯坦的呼声陡然升高,尤其是英国、法国等欧洲大国姿态较之前有明显转变,使以色列面临的外部压力显著增大。在海外的犹太人群体也面临日益严峻的安全压力。比如在10月2日,英国曼彻斯特一座犹太教堂发生恐怖袭击,造成死伤。过去两年里,全球多国的犹太人群体多次遭到各类袭击威胁。
此外,以色列最大靠山也是最坚定支持者美国的态度也出现一些变化。面对加沙冲突造成的巨大平民伤亡和人道灾难,美国“形单影只”偏袒以色列,也因此背负了巨大的外交压力。此外,以色列对卡塔尔境内哈马斯目标的打击,加剧了地区伙伴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信任。
在此情形下,美国就结束加沙冲突提出一份文件——“20点计划”,以此为基础,在埃及、卡塔尔、土耳其等国共同斡旋下,推动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开罗达成了停火协议。尽管当前停火协议的执行和后续谈判仍面临诸多挑战,但实现加沙地带的短暂停火,仍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民带来了一缕和平的曙光。
(作者系西北大学以色列研究中心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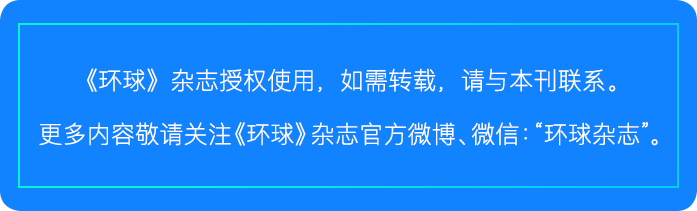

 手机版
手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