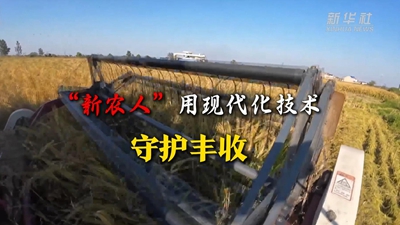北京协和医院心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吴炜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冠心病的形势正在发生变化。“有时候我们在导管室里做着做着手术,会发现台上的患者年龄比医生还小。”他说,这并不是个案,而是一种正在悄然显现的趋势。
冠心病不再只是中老年人的疾病。吴炜在接受新华网专访时,从流行趋势、症状识别、风险管理、介入治疗、康复方式到个体化用药,进行了深入解析,也纠正了一些社会上流传已久的误区。

患者数量仍在增长,年轻化渐显
如果说十几年前,大多数冠心病患者仍集中在中老年群体,那么现在,三四十岁的中青年已经不再罕见。他强调,公众之所以觉得年轻人发病突然,多数是因为没有意识到冠心病并非“突发疾病”,而是多个危险因素长期累积的结果。冠心病发病总量在上升,这背后不仅是人口老龄化,还有长期生活方式和慢性病管理产生的沉积效应。
让他印象尤其深刻的还有城乡差异。“很多人以为城市白领心梗多,是因为媒体报道常见,但实际上农村地区发病率更高,只是知晓率低,也缺乏规范治疗。”
至于年轻化,他认为并不是“疾病下沉”,而是危险因素提前累积。“熬夜、久坐、外卖、吸烟、高油饮食、情绪压力大、缺乏体检,这些因素把原本五六十岁才会爆发的风险提前十年、二十年。”但在总体发病构成中,中老年人仍占主力,只不过年龄边界不再像以前那样清晰。
胸痛≠心梗,哪些信号必须就医?
胸痛是公众最常联想到冠心病的症状,但在吴炜看来,正是“怕得不对、忽视得不准”导致不少误判。他解释,冠心病和急性心梗确实会引起胸痛或胸闷,但反过来,胸痛并不必然意味着心血管问题。在大型三甲医院的胸痛急诊中,真正最后确诊为冠心病的患者不到三分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警惕是多余的,而是需要更清晰地识别心源性疼痛的特征。
他提到一个临床上的常见判断经验:如果一个人能用手指明确指出胸口某个点疼,那么这个疼痛往往不是来自心脏,因为心脏属于内脏器官,其疼痛定位并不精准。同时,一两秒钟的刺痛、电流感、扎一下就没了的感觉,也大多不是缺血性表现,多见于肌肉、神经或体表组织。而真正心脏缺血导致的胸痛,在运动、快走、爬楼、背重物时最易诱发,持续时间相对较长,休息后逐渐缓解,严重时还可能伴随胸闷、出冷汗、咽部不适或向肩膀、下颌、牙齿放射。
吴炜提到,患者不需要自己分辨所有诊断类型,但当胸部不适超过二十分钟、伴随呼吸困难、恶心、咽部紧缩或放射性疼痛时,不要犹豫。“尤其是有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肥胖、吸烟或者有心脑血管家族史的人,如果突然胸痛但说不清位置、也描述不出性质,就应该尽快就医。”
谁是高危人群?可控因素和不可控因素都要注意
关于高危人群,吴炜将冠心病的危险因素分为“不可改变的”和“可改变的”两类。年龄、性别和家族史是无法调控的背景变量,如男性在中青年阶段发病率高于女性,但女性绝经十年后逐渐追平。遗传因素的影响不容忽视,多基因累积效应在一些家族中表现明显。但他更强调的是可干预因素,其中“三高”、吸烟、肥胖、缺乏运动、情绪压力、饮食结构失衡都是冠心病进展的“加速器”。
他指出,不少人仍习惯把慢性病当成“短期干预型疾病”,期待“一次吃药好几年”“控制两个月就能停药”,这是一种危险误区。“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不是感冒,也不是肺炎。它们本质上不能根治,只能被长期控制。如果控制好,风险就压住了;如果反复波动,就在为冠心病埋雷。”
冠心病患者的血脂控制目标不是一刀切,而是分层管理。例如,没有危险因素的人群,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控制在3.4以下即可;若合并高血压或超声发现颈动脉斑块,则需降至2.6以下;一旦确诊冠心病或做过支架,目标值降到1.8以下;如果曾发生心梗、合并糖尿病、多支血管病变甚至脑卒中,则应降到1.4以下。“有人觉得数字小得不现实,但越高危的人越承受不起血脂的继续攻击。”
做过支架怎么康复?别把自己当病秧子
提起冠心病就不可避免提到支架。吴炜说,大众最大的误解之一,就是“血管堵了就得放支架”“放完支架就不怕心梗”。他解释,支架真正发挥作用只有两种情况:第一,发生急性心梗,需要紧急开通血管防止心肌大量坏死;第二,出现明显劳力性心绞痛,影响日常生活和心功能。“如果一个人血管堵得七八成但没症状,也没有反复胸闷胸痛,那么预防性去放支架并不能减少他发生心梗的概率。心梗本质上不是堵到百分之八十、九十才发生,而是斑块破裂后形成血栓堵死血管。”
吴炜强调,支架不是“预防针”,也不会替代药物治疗。很多人担心“放支架就要一辈子吃药”,他解释:“心梗病人不管放不放支架,药物都是一样要吃的。降脂、抗血小板、控制血压血糖,一个都不能少。”如果是没有心梗、仅因狭窄症状放支架的患者,只是在术后一段时间加到两种抗血小板药,长期方案仍然要回归基础病管理。
对于患者关心的术后生活,吴炜态度很明确:没有心梗和心衰的患者,术后恢复良好,本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和运动。“很多人以为放了支架不能动,这是误解。真正限制他们活动的不是支架,而是没有治疗前的胸痛。”他鼓励术后逐步恢复慢跑、骑车、游泳等中等强度运动,同时提醒要避免极端刺激,如蒸桑拿、蹦极、极限过山车、深潜等。如果存在心衰,则需在医生和康复医疗科的指导下制定运动处方,控制心率和运动负荷,逐步恢复功能。
精准用药还在探索期,但协和医院“个体化治疗”已落地
过去几年,“精准用药”一词逐渐进入公众视野,部分患者误以为冠心病已经可以通过基因检测“一人一药”。吴炜指出,目前在冠心病领域,真正意义上的基因指导用药还没有形成大规模循证依据。“有一些小样本研究探索了抗血小板药物代谢基因和药效关系,但扩大人群后临床效果并不稳定,不足以替代指南推荐。”他认为,目前更现实、更有价值的仍然是个体化治疗。
所谓个体化治疗,并不是盲目创新,而是基于病人的具体情况做合理调整。例如育龄期女性的降压治疗要避开对胎儿有致畸风险的药物;对长期高盐饮食、嗜酒、肉类摄入量大的男性患者,医生会加强利尿和饮食干预方案;合并肿瘤、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或存在手术计划的患者,则需要与外科、麻醉科、消化科、风湿免疫科等多学科合作,根据风险和时机设计治疗顺序。“很多复杂病例不是靠一个科室解决的,而是靠综合判断找到最合适、不是最激进的方案。”
吴炜谈及北京协和医院在冠心病介入治疗方面的优势时强调,“协和医院的特点不是单项技术,而是多学科的整体评估能力。”许多冠心病患者合并肾病、肿瘤、血液病、风湿免疫病等复杂病情,在专科医院难以得到全面方案。“我们会组织多学科会诊,把血管情况、手术风险、药物影响、其他脏器病变统一评估,给出最佳方案。”
别再误解支架、他汀和药物治疗了
谈到公众认知误区,吴炜坦言,最麻烦的不是疾病本身,而是错误信息和断章取义。一些人把网络短视频当“医疗结论”,看到“国外都不用支架了”“斑块可以整体切除吸出来”就轻信。“那些视频很多是动画演示,斑块在体内往往像石头一样硬,不可能像吸血块那样完整取出。目前支架植入依旧在美国、日本、欧洲等国家广泛应用。”
关于他汀类药物,吴炜也经常被问起“会不会伤肝”“会不会致癌”“会不会升血糖”。他解释,中国人确实比欧美人群更容易在服药初期出现转氨酶升高,但这是可监测、可撤药、可逆的。“就像有人吃芒果会过敏,但你得先吃了才知道自己会不会过敏。”至于“服药导致肿瘤”,他说那是因为这些患者因为预防或者控制了心梗和卒中而活得更久,肿瘤是在寿命延长的背景下发生的,不是药造成的。血糖轻度升高则远远小于他汀类药物对动脉粥样硬化的保护效果。
吴炜最后强调,冠心病不是突然来的,也不是靠一次体检或一次支架就能彻底摆脱的。“真正让风险下降的,是长期控制慢病、改善生活方式和规范治疗。不要等第一次胸痛、第一次心梗才开始重视,也不要指望一个操作就把未来十年二十年的危险抵消。”